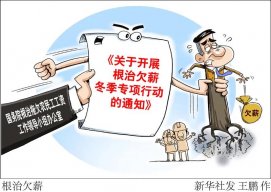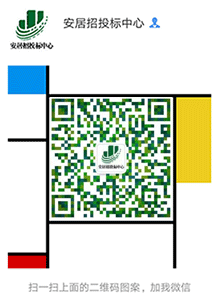安居推送:最高法院:执行董事私刻公司公章与他人签订借款合同是否有效?
发布时间:2021-10-26 08:39
执行董事在无代表或代表权限下以公司名义与相对人签订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
阅读提示
公司印章作为公司对外进行意思表示的手段,在商事交易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经营活动中,持有盖着公司印章的法律文件的民事主体会被认定为公司的代理人。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公司印章丢失、员工私刻印章、印章交接程序混乱以及印章效力与签字效力关系混乱等问题。是否加盖公司印章对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成立、生效起着重要作用,缺少合理的印章管理制度会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进而导致法律纠纷的产生。
裁判要旨
相对人轻信无权代理人职务身份以及自行刻制的公司印章便与其签订借款合同,可认定其存在过失,不构成表见代理,执行董事代理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该合同对其所在公司不发生法律约束力。
案情简介
一、2014年4月1日,尹某(出借人)与贵州A公司(借款人)、贵州B公司(借款人)、浙江省C公司(担保人)、曹县D公司(担保人)签订《借款担保协议书》,约定借款金额为500万元。
裁判要点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的裁判要点归纳如下:
第一,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取决于以下两个要件事实的认定:无权代理人是否具有代理权的外部表征和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否出于善意且无过失。
第二,樊某本人作为B公司执行董事无代理权,在B公司法定代表人不知晓的情形下,私刻印章并以该公司名义订立案涉协议。该枚印章,虽非B公司公章但确曾对外使用,具有代理权的部分外部表象。
第三,当事人以代理方式实施法律行为,代理行为的相对人应当核验“人与章是否一致”“印与信是否相符”。尹某出借520万元,未审核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樊某的职务身份,仅以印章和执行董事身份轻信樊某有该公司的代表权或代理权,并与之签订《借款担保协议书》,主观上明显存在过失。综上所述,上述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借款担保协议书》对B公司不发生法律约束力。
实务经验总结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的专业律师团队办理和分析过大量本文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量办案同时还总结办案经验出版了《云亭法律实务书系》,本文摘自该书系。该书系的作者全部是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战斗在第一线的专业律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该书系的选题和写作体例,均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为主,力图从实践需要出发,为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法律问题,寻求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本文所引述分析的判例也不是指导性案例,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中并无约束力。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例的细节千差万别,切不可将本文裁判观点直接援引。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不同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和研究,旨在为更多读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观察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文案例裁判观点的认同和支持,也不意味着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该等裁判规则必然应当援引或参照。)
相关法律规定
《民法典》
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10月26日实施]
第十三条 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失效]
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失效]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法院判决
以下为法院在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对该问题的论述:
C公司所称表见代理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该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其中,判断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取决于以下两个要件事实的认定:客观上,行为人即无权代理人是否具有代理权的外部表征;主观上,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否出于善意且无过失。这两个要件同时具备,方可构成表见代理,使得无权代理取得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
案件来源
尹某、浙江省C公司、浙江省C公司贵州分公司与贵州B公司、贵州A公司、曹县D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70号]
延伸阅读
在检索大量类案的基础上,云亭律师总结相关裁判规则如下,供读者参考:
1
公司高管未获得授权情况下,以公司名义对外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相对人未核实其代理权限则不能认定为善意相对人,该代理后果由公司高管个人承担。
案例一:张某与广西A公司、广西A公司西宁分公司、韩某、青海B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529号]认为,“根据案涉《承包经营协议书》载明的内容,韩某仅是A公司聘任经营A公司西宁分公司的经营经理,并非A公司西宁分公司的负责人;韩某以A公司或其分公司等名义对外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等,须事先获得A公司的盖章同意;韩某向A公司缴纳管理费,经营期间自负盈亏。张某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在协商借款时,韩某向其提供了《承包经营协议书》等,故张某对《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上述内容应属明知。《借款抵押协议》上无A公司的盖章,A公司、A公司西宁分公司对此亦不认可。张某也未举证证实韩某以A公司西宁分公司名义向其借款系经A公司明确授权或事后追认。故韩某在《借款抵押协议》上加盖印章的行为,不属于A公司西宁分公司负责人的代表行为,亦不属于有权代理行为。张某在韩某向其提供《承包经营协议书》后,A公司、A公司西宁分公司未明确授权或同意韩某以其名义对外借款的情况下,向韩某个人账户给付借款,且借款中包含部分韩某前期借款。据此,张某不属于“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善意合同相对人,韩某在《借款抵押协议》上盖章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二审判决由韩某个人承担还款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张某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二:金某与泗阳A公司、苏州B公司、汪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464号]认为,“汪某以A公司的名义向金某出具借条借款1000万元,泗阳A公司是否应承担该借款偿付责任,尚需进一步审查认定金某在出借款项过程中是否有理由相信汪某有代表泗阳A公司对外借款的权利表征,即是否善意无过失。在表见代理制度中,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无过失,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分析认定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就本案而言,在汪某不是泗阳A公司法定代表人、亦非泗阳A公司股东的情况下,金某在出借案涉款项时并未核验汪某是否获得泗阳A公司对外借款的授权书或者相关证明文件,更未向泗阳A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核验汪某的代表身份;金某在明知借条载明的借款人为泗阳A公司,在没有向泗阳A公司进一步核验的情况下直接基于汪某以泗阳A公司名义出具的委托书,将案涉款项汇入汪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苏州B公司(借条上注明的担保人)。由此,二审判决认定对于汪某能否代表泗阳A公司对外借款,金某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非善意无过失,汪某对外借款行为不构成对泗阳A公司的表见代理,有相应的依据。”
案例三:刘某与冉某、重庆A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613号]认为,“关于A公司是否应当就冉某对刘某的还款义务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所涉担保为公司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系单务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公司担保行为具有诸多限制,交易相对人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对于相关人员代表或代理公司对外从事担保行为的权限是否受法律规定限制,具有一定的审查义务。本案中,即便冉某的确为A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刘某在接受A公司担保,特别是冉某作为行为人,以A公司名义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应当对冉某的行为是否具备相应权限做必要的审查,至少尽到形式审查义务。而刘某作为合同相对人,并未审查A公司提供担保是否有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故其未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因此,一、二审法院认定冉某伪造A公司印章对案涉借款提供担保不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
2
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借款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所涉借款合同对被冒名者没有约束力,被冒名者不承担相关的还款责任。
案例四:彭某、都某与张某、朱某、朱某燕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149号]认为,“关于朱某与彭某、都某之间是否建立借款及抵押关系的问题。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法律制度。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作为两个主体对相对人而言都是明知的,亦即相对人明知行为人与责任主体不一致,而冒名行为是行为人以他人名义从事民事行为,对相对人而言只有一个主体,其主观意识是认为行为人与责任主体是一致的,二者存在明显区别。在本案中,首先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的《借款/担保合同》系朱某燕冒用“朱某"名义与彭某、都某签订,而朱某本人对此并不知情,朱某事后也予以否认,故朱某并未与彭某、都某之间具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其次,虽然彭某、都某认为朱某向朱某燕提供房产证以及身份证前明确知晓朱某燕将使用房屋进行抵押贷款的事实而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但即使能够认定朱某同意朱某燕使用其房屋进行抵押贷款,也不能证明朱某就同意朱某燕冒充自己的名义签订借款及抵押合同,更不能证明朱某就有与彭某、都某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最后,虽然彭某、都某主张朱某燕的冒名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表见代理性质系无权代理,其外观系行为人以代理人的身份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代理人所从事之法律行为之法律效果应归属于被代理人,而本案系朱某燕以朱某的名义签订合同的冒名行为,并非以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合同,故朱某燕冒用朱某的名义向彭某、都某借款这一行为无表见代理的外观,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也无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空间。据此,朱某与彭某、都某之间并未建立借款及抵押关系,本案所涉《借款/担保合同》对朱某没有约束力,朱某不应承担相关的还款责任。”
3
当事人使用盖有公司印章的空白借款合同与特定人成立借款关系后对公司具有法律效力。
案例五:湖北A公司、孙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111号]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A公司与孙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某新系A公司的前股东,且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远的父亲,涉案《借款协议》系李某新代表A公司签订,A公司对此没有异议。从A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李某新的询问笔录来看,李某新对借款2400万元的事实并未否认,只是称其不认识孙某,其是向杨某借款,并将签章后的合同交给杨某,交给杨某时,《借款协议》上的出借人及利率约定均是空白的。关于为什么合同上没写借款人,李某新回答“杨某称:没事,把钱给到位就行了"。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李某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清楚、理解合同内容,同时也表明其放弃核实债权人的身份信息,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主观上具有与不特定的债权人成立借款关系的意思表示,空白借款合同的相关内容被明确后,对A公司理应具有约束力。二审认定李某新曾将盖有A公司印章的空白借款合同提供给案外人委托其代为借款,A公司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予合同相对方,其行为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概括性授权并无不当。本案针对同一借款事实虽存在两份《借款协议》,但无论借款期限的约定为“十天”或“一年”,在孙某已经履行出借2400万元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均不影响《借款协议》的效力。如前所述,在李某新将出借人及利率约定均为空白的《借款协议》交给杨某后,《借款协议》上出借人孙某的签名、利率“月2.4%”虽系事后添加,亦不影响双方之间《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二审认定A公司与孙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
4
公司变更名称后在借款合同中使用公司变更前的印章不影响借款合同效力。
案例六:贵州A公司与周某、王某、黔西B公司及C煤矿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572号]认为,“关于B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案涉两份《借款合同》分别于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1月20日签订,合同中加盖的均是“C煤矿"印章。虽然C煤矿已于2011年变更为C公司,但经查明,C煤矿作为转让人与作为受让人的B公司于2013年9月9日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加盖的亦为“C煤矿"印章。表明C煤矿在变更过程中确实存在印章使用不规范的情况,故不能仅据此否认其借款人的身份。不仅如此,经一审法院查明,C煤矿对案涉两笔借款均予以确认,且C煤矿已实际偿还了部分本息,故二审法院认定C煤矿为真实借款人并无不当。C煤矿作为B公司设立的分公司,其所欠债务理应由B公司承担。”
5
公司负责人以公司名义与善意相对人签订合同,该行为对公司有效。公章是否伪造,不影响合同效力。
案例七:A公司与金某、胡某、浙江B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17号]认为,“关于是否存在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新证据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系伪造的问题。A公司在申请再审中提交了《立案告知书》作为新证据,认为《借条》加盖的印章系伪造,担保不成立。根据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胡某在2016年1月1日的《借条》上签字并加盖A公司西安分公司印章时,胡某系A公司西安分公司的负责人,金某有理由相信胡某有权代表A公司西安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即便该《借条》上A公司西安分公司的印章虚假,胡某的盖章行为也可视为公司行为,原审判决认定由A公司西安分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A公司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